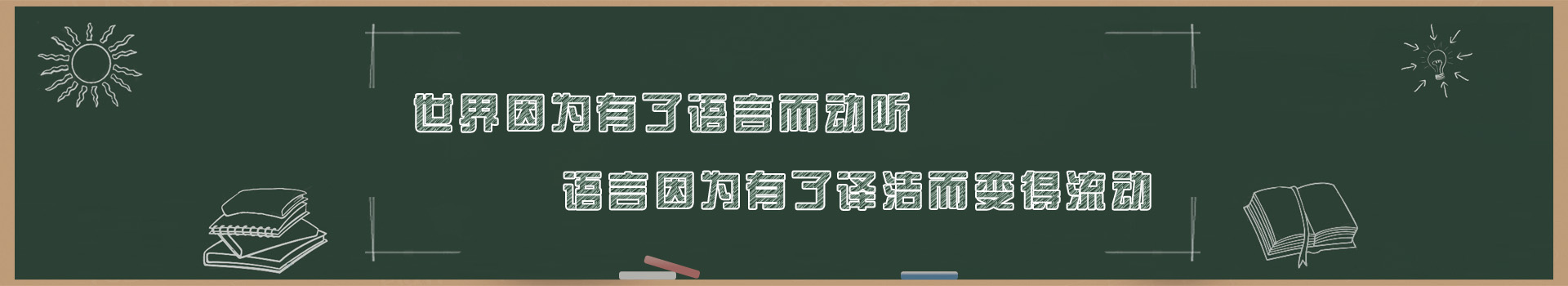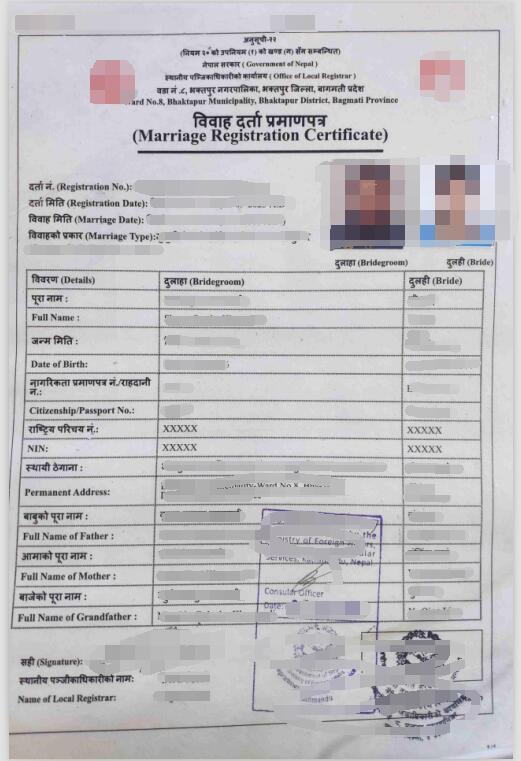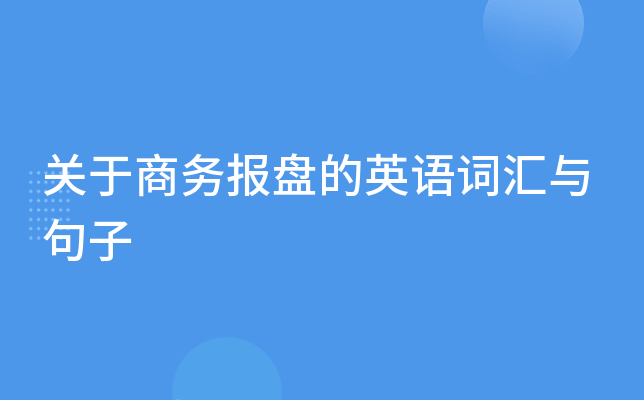翻譯新聞 News
如何發現翻譯慣例
來(lái)源:網絡 作(zuò)者:本站 發布時(shí)間(jiān):2022年12月12日 閱讀次數(shù): 次
為(wèi)了比較兩個(gè)不同時(shí)代或文化社群普遍的翻譯慣例(曆時(shí)vs共時(shí)),我們如何描述某一時(shí)代(如德國20世紀90年代前期)盛行(xíng)于某一文化社群的普遍翻譯慣例?如果對普遍的翻譯慣例一無所知,便不能對任何具體(tǐ)譯文作(zuò)出公允的評價。
以你(nǐ)所期待的嚴格意義上(shàng)的翻譯(用你(nǐ)自己本國文化當今的标準)來(lái)和(hé)以下這段話(huà)相比較。
例1:
在16世紀的西班牙,為(wèi)了使普通(tōng)大(dà)衆一目了然,譯者常常在原文的基礎上(shàng)加大(dà)量解釋或者用疊句或諺語的方式表述和(hé)原文有關的神話(huà)或名著典故,以使譯本更加具體(tǐ),這是當時(shí)非常普遍的現象。所以F. 馬德裏(Fernández de Madrid)翻譯的《伊拉斯谟》(Erasmus)幾乎是原文篇幅的兩倍也就不足為(wèi)奇了(參見Barrass,1978:195)。
由于翻譯慣例不是明(míng)文規定,要确定它們何時(shí)、怎樣運作(zuò)似乎非常困難。以下簡要討(tǎo)論幾種可(kě)能奏效的方法。
(a) 對現有譯文的分析
某知名譯界學者最近在談到翻譯理(lǐ)論時(shí)說:“我們之所以知道(dào)什麽是翻譯,是通(tōng)過大(dà)量現有的譯文。”果真如此麽?在分析現有的目标文本時(shí),我們永遠不能确定這篇翻譯是否真的反映了一個(gè)慣例,還(hái)是體(tǐ)現了譯者自身的意圖。我們需要大(dà)量的例證來(lái)排除其他變量(決定翻譯形式與質量的因素),如:譯者的專業能力或發起人(rén)下達的具體(tǐ)翻譯說明(míng)(instruction)。曆史翻譯學或描述翻譯學的學者在文學翻譯研究中都選擇了這一方法(參見Frank&Schultze,1988:96)。
(b)翻譯評論
人(rén)們會(huì)認為(wèi)對譯本的評論不僅會(huì)反映評論者對譯文的判斷,同時(shí)還(hái)能體(tǐ)現出人(rén)們對所譯文本類型翻譯的普遍期待。但(dàn)是當評論提到翻譯本身,往往流于表面(譯本通(tōng)常被視(shì)為(wèi)原作(zuò)),泛泛而談。例2選自菲利普·迪昂(Philippe Djian)的小(xiǎo)說《巴黎野玫瑰》(Betty Blue)的英譯本評論,事實上(shàng),全文隻有一處提到這本書(shū)是譯作(zuò)。
例2:
譯者巴特勒(Howard Butler)成功做(zuò)到與原作(zuò)精神保持一緻 (Sunday Times Books, 1990. 1.1.p. H13)。
例3:
(弗吉尼亞·伍爾夫短(duǎn)篇小(xiǎo)說的德語新譯本)緊緊追随原文的步伐……對原文的地位毫無僭越(Die Zeit,1989.11.11.p.85)。
(c) 翻譯理(lǐ)論的陳述
翻譯理(lǐ)論和(hé)方法上(shàng)的觀點,不論是理(lǐ)論家(jiā)還(hái)是實踐者提出的,至少(shǎo)能部分地或從側面反映普遍的翻譯觀念,不過上(shàng)文提到的問題依然存在,慣例和(hé)個(gè)人(rén)觀念較難區(qū)分。
例4:
逐字逐句或行(xíng)間(jiān)釋譯的《聖經》譯本是翻譯的本質或理(lǐ)想狀态 (Benjamin, 1972:21)。
本雅明(míng)(Walter Benjamin)的這一論斷也許并不是要我們抛開(kāi)路德的《聖經》譯本,去讀文法不通(tōng)、逐字對應的譯本。他隻是指出一種理(lǐ)想狀态---逐字翻譯(interlinear translation)可(kě)以得(de)到可(kě)讀性強,又能被接受的功能“對等”的目标文本。
至少(shǎo)就語用層面(這裏指功能)來(lái)說,其他的觀點更直白,盡管并未提及形式。
例5:
對于機械維修文件之類技(jì)術(shù)性翻譯而言,優秀譯作(zuò)的标準就在于它所傳達的信息和(hé)知識的數(shù)量。在操作(zuò)層面,評判的标準就是譯文使用者能否像原文使用者一樣對裝備進行(xíng)維修。(Brislin,1976:14)
在我看來(lái),關于譯論或譯法的陳述,最有趣的觀點莫過于譯者對自己翻譯活動的評價。通(tōng)常譯者不必對自己的譯文作(zuò)評論,除非感到譯文可(kě)能有悖讀者的期待。
(d) 譯文使用者的介入
就翻譯而言,其“社會(huì)化過程”不僅指我們閱讀譯文的經曆(從使用說明(míng)、電(diàn)腦(nǎo)手冊到古典戲劇(jù)),而且包括我們在學校(xiào)的語言教學過程。因此,“标準”的譯文使用者所持的普遍翻譯概念極具模糊性,有關讀者期待的問題都隻能在具體(tǐ)的情境下作(zuò)答(dá)。
(e) 多(duō)語譯本的比較
總的說來(lái),尋找盛行(xíng)于某一文化社群普遍的翻譯觀點似乎頗為(wèi)棘手,因此,我建議使用從下至上(shàng)的方法:從遇見的具體(tǐ)翻譯問題開(kāi)始,解決這些(xiē)問題的方法往往是由規範性慣例決定的 (主要是語用層面的跨文化翻譯問題,參見Nord,1987)。
通(tōng)過比較同一原文的不同語種的譯本,我們可(kě)以看到,不同譯語文化中處理(lǐ)同一翻譯問題時(shí)有各自不同的途徑。從它們對問題的一般或大(dà)部分解決方法,我們也許能推測出更普遍的創構性慣例,比如關于文本類型和(hé)翻譯類型之間(jiān)的關系。
盡管如此,對這些(xiē)具體(tǐ)問題的分析還(hái)是能使我們接近創構性翻譯策略。對比西班牙語和(hé)德語文學作(zuò)品中對個(gè)人(rén)姓名的翻譯,我們可(kě)以看出兩種不同文化迥異的慣例。
例6:
在文學文本的德語譯文中,個(gè)人(rén)姓名(包括教名)通(tōng)常保持原文的形式不變(當然,我們應該考慮到,在德語中的同名,讀者會(huì)在發音(yīn)上(shàng)略作(zuò)改動)。外國名字用來(lái)“突顯”故事的文化背景。在西班牙語的文學翻譯中(或在西班牙文學中),教名通(tōng)常用西班牙語形式,人(rén)們似乎對出現一個(gè)法國姓和(hé)西班牙教名組成的名字毫不介意。在馬克斯·奧伯(MaxAub)創作(zuò)的西班牙戲劇(jù)中,以法國為(wèi)背景,那(nà)些(xiē)法國人(rén)的名字是Josefina Claudio, señora Bernard 這樣的法西混合形式,但(dàn)在該劇(jù)的德語譯本中,這些(xiē)人(rén)名變成“Joséphine”、“Claude”和(hé)“Madame Bernard”這樣地道(dào)的法國名字(參見Aub,1972)。
濰坊翻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