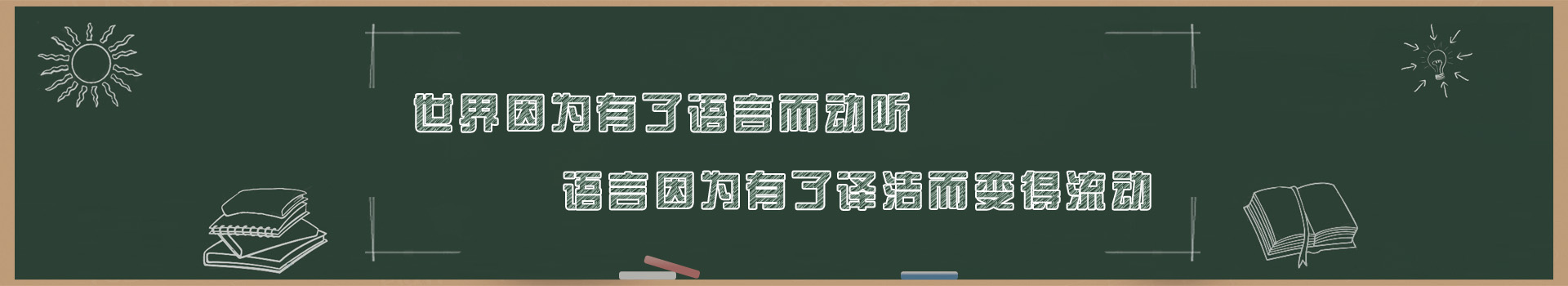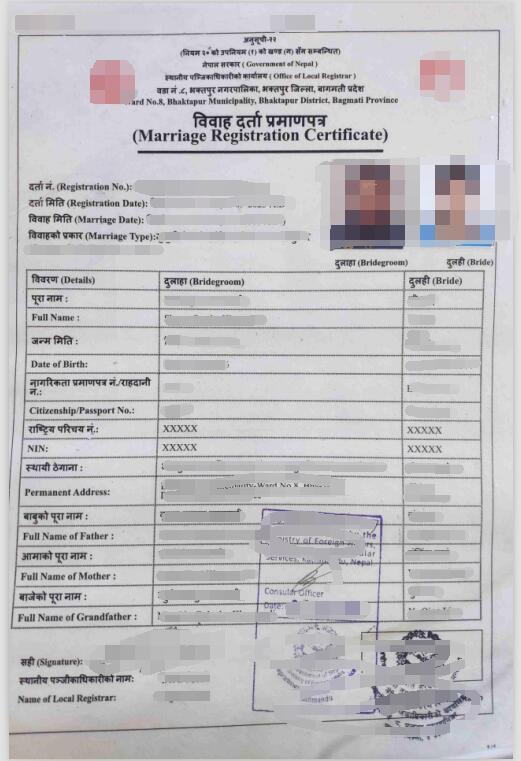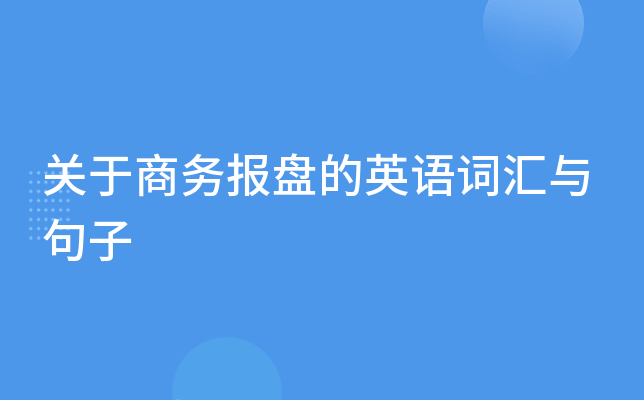翻譯新聞 News
譯本比較的批評方法
來(lái)源:網絡 作(zuò)者:本站 發布時(shí)間(jiān):2023年03月21日 閱讀次數(shù): 次
很(hěn)多(duō)翻譯論著中都介紹過譯本比較這一方法,有論者甚至以譯本比較為(wèi)核心概念,提出要建立“比較翻譯學”。筆者認為(wèi),如同“比較文學”、“比較法學”等學科名稱一樣,“比較翻譯學”應是指不同語言、不同文化或不同國别翻譯理(lǐ)論研究之間(jiān)的比較,而譯本比較主要還(hái)是一個(gè)方法的概念。
“比較”是相對于單獨分析一部(篇)譯作(zuò)而言,一般指同一原作(zuò)的兩部(篇)以上(shàng)譯作(zuò)之間(jiān)的比較。這種比較中雖然總會(huì)涉及譯作(zuò)和(hé)原作(zuò)之間(jiān)的比較,但(dàn)兩者的性質不同:原作(zuò)一譯作(zuò)比較從根本上(shàng)說是兩種語言文化系統之間(jiān)的比較,而不同譯本之間(jiān)的比較除此之外,還(hái)有屬于同一種語言文化系統內(nèi)部的比較。另外,由于将譯作(zuò)與原作(zuò)相比較是譯者和(hé)批評者不言而喻必然要做(zuò)的事,它也稱不上(shàng)是一種批評方法。換言之,它就是“批評”本身,而不是批評的“方法”。
譯本比較要有說服力,必須講究比較的方法,講究論證的可(kě)靠。作(zuò)為(wèi)一種起碼的要求,無論什麽比較或對比,都必須選擇适當的對比項,并使之具有可(kě)比性。比如,要判斷一部漢語作(zuò)品語言的可(kě)讀性,如果采用的是基于英語語言的一個(gè)可(kě)讀性級次表(如根據句子長度、連接詞的多(duō)少(shǎo)、某種等級的常用詞使用比例來(lái)判斷可(kě)讀性),那(nà)麽就需要考慮:這種判斷方法是否也适用于漢語?由于漢語具有“意合”的特點,連接詞的使用能不能用來(lái)作(zuò)為(wèi)判斷可(kě)讀性的一個(gè)指标,是需要對漢語的相關現象作(zuò)專門(mén)研究才能确定的,直接照搬英語的判斷方法就不一定合适。這是對比語言學的一個(gè)例子,譯本比較同樣如此,也需要注意可(kě)比性的問題。
比如,如果兩個(gè)譯本所依據的原作(zuò)版本不同,譯本中出現了差異,就必須弄清是不是版本差異造成的問題,否則就不能下結論。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該盡量使用依據同一版本原作(zuò)的譯作(zuò)來(lái)進行(xíng)比較。
又如,譯本比較必須考慮曆史因素,以九十年代的譯本來(lái)批評四十年代譯本的語言,顯然是有失公允的。由此産生(shēng)橫向(共時(shí))比較和(hé)縱向(曆時(shí))比較之分。橫向比較主要有兩種:
1. 以一譯本為(wèi)主,其他譯本為(wèi)次。這種比較中的其他譯本一般是作(zuò)為(wèi)參照的,評論的重點是一種譯本。如評孫緻禮譯的《傲慢與偏見》(1990譯林版),以張玲、張揚譯本(1993人(rén)民文學版)和(hé)義海譯本(1994海峽文藝版)為(wèi)參照。
2. 兩種(或兩種以上(shàng))譯本平行(xíng)比較。
縱向比較也有兩種:
I. 同一譯者不同時(shí)期的譯本比較。如比較劉重德《愛(ài)瑪》的1949年初譯本和(hé)1993年的重譯本。
II. 不同譯者不同時(shí)期的譯本比較。如将1957年出版的張谷若譯《苔絲》(人(rén)民文學版)和(hé)1994年的孫法理(lǐ)譯本(譯林版)作(zuò)比較。
對比項、可(kě)比性都是具有方法論色彩的概念,對比語言學正是在這些(xiē)概念的基礎上(shàng),建立起了自己的方法論體(tǐ)系,推進了學科建設。在對譯本進行(xíng)比較時(shí),這些(xiē)概念也可(kě)以為(wèi)我們提供一些(xiē)方法論方面的依據。
威海翻譯公司